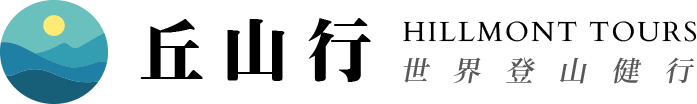文.圖 / 林學聖
在溫暖的南台灣冬日,我們跟隨著族人腳步,沿著88風災後每年變換的路徑,前往禮納里魯凱族人夢裡的故鄉 -「舊好茶」。

白裡透紅的野芙蓉在身旁盛開,鹽膚木的果實嘗起來酸酸鹹鹹,令人驚訝的是沿途看到不少咖啡樹,結實纍纍,瑞珍笑說這些咖啡都是猴子種的。原來日治時期舊好茶就有種植咖啡樹,後來動物們的排遺把咖啡樹繁衍在整個山區。瑞珍三不五時就會上山採集野生的咖啡豆,自己烘培販售,取名「獼猴咖啡」。
半天路程抵達舊好茶。部落入口現在只有新砌的石椅,連老雀榕也沒了。部落依山而建,斜坡上座落著一百多間石板屋,全盛時期人口有七八百人。1978年遷村後,石板屋因橫樑腐朽造成屋頂塌陷,四周植物蔓生,好像台灣版的馬丘比丘,漫步其中彷彿自己就是探險家。現在只有三、四間房子有族人重修後搬回來住。

部落的最高處是小學遺址,周圍都是茂盛的王爺葵,現在也只剩水泥牆柱。司令台後方有一座石碑,上面依稀可見被磨去的「南幅重助」四字,還有被抹去的「毋忘在莒」油漆痕跡。歷史就是在不斷地互相抹滅記憶中,無畏地前進著。
原來南幅重助是日治時代的小學老師,自殺身亡後,日人特別立碑紀念。在那互相碰撞的時代,一個遠渡重洋離鄉背井的老師,來到偏僻的蕃地,是在怎樣的心情下結束自己的生命呢?
下午下起大雨來,說好的北大武山應該還矗立在前方山谷的雲霧中。我們今天在邱爸的房子裡過夜。邱爸的魯凱名字是「奧威尼」,是有名的魯凱族詩人,我們一邊品嚐烤豬肉一邊喝酒閒聊。

「您為什麼要搬回舊好茶呢?」
「那是1990年的事了。我一直夢到爸爸的房子,屋頂都不見了,我想念他,就回來重建老房子。我把門簷做的低一些,適合158公分高的爸爸。每當低頭進門時,就會想起爸爸。」
「您現在還寫作嗎?」
「還是想寫啊! 有時月光太美,我出門看月亮,看著看著時間就過去了。我貪戀月光,耽誤了寫作。」
「真不好意思,我們借住您的房子,怕晚上打呼會吵到您。」
「睡覺打呼是生命在唱歌啊! 怎麼可以責備自然的歌聲呢?」
在詩人的眼中,所有事物都可以是美的、無可責備的。
石板屋內升著火,很溫暖,有昔日熟悉的淡淡煙燻味。從前魯凱族人與許多原住民族一樣,家人死後就直接埋葬在屋內地下,永遠跟摯愛的親人在一起。我們今晚也跟邱爸的祖先們睡在一起,在他們的庇護下進入夢鄉。
畫面回到小學遺址。在南幅重助的紀念碑後面有一座墓園,是當年日本人建的,希望族人死後就葬在那裡,不要埋在家中。據說第一位族人下葬墓園時,全村的人都哭了,因為明白自己以後也會像這樣,被家人遺棄在外面。相反的,我們漢人期望親人死後趕緊上路,不要再回來。我們為什麼要畏懼呢?